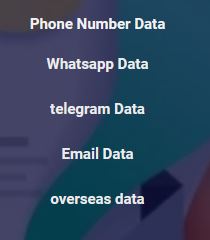中国根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公约》、《儿童权利公约》以及其他国际人权和相关条约所承担的人权义务同样适用于域外,这有利于中国积极规范“一带一路”国家的商业活动,以防止侵犯这些条约所保护的国际人权(《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 2、3 和 5 条;《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 2 和 3 条;《禁止酷刑公约》第 2 条;《儿童权利公约》第 2、3 和 5 条)。国际法院早已在《南非继续驻扎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一案中确认,各国有义务防止在其领土之外发生违反人权的行为,法院宣布:
“南非对造成并维持法院认定为合法非法。因此,南非有义务撤出对纳米比亚领土的管理。南非维持目前的非法局面,并在无权的情况下占领该领土,因持续违反国际义务而承担国际责任。南非还应对任何违反其国际义务或侵犯纳米比亚人民权利的行为负责。南非不再拥有管理该领土的任何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南非可以免除其根据国际法对其他国家行使与该领土有关的权力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对领土的实际控制,而不是主权或所有权的合法性,是国家对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承担责任的基础。 ”(斜体添加,第 118 段。)
同样,国际法院在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一案的咨询意见中强调了国际人权条约的域外适用:
“……法院认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适用于一国在其领土之外行使管辖权时实施的行为……《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既适用于一国拥有主权的领土,也适用于该国行使属地管辖权的领土。”(斜体添加,第 107-111 段)。
中国利用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独特的主权贷 瑞士资源 款合同实践,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不同形式主张某种事实上的领土管辖权或行使重大主权控制,无论是通过运营控制还是通过长期或永久租赁收购海外港口(如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或中国在吉布提港建设的海外海军基地);向空壳公司提供基础设施项目贷款,使负债累累的国家避免报告由主权担保支持的债务,而这些债务最终需要通过公共基金偿还;要求使用一国的自然资源或一国的海外托管账户为“一带一路”贷款提供深度抵押,这些抵押可随时用于执行、扣押、查封或没收;并强制在所有海外“一带一路”项目的执行、履行和实施中独家实施或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2023 年 3 月 22 日对中国第三次普遍定期审议的结论性意见中指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域外影响,并对“有关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供的贷款做法和条件对第三国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产生负面影响的报告”表示担忧(第 22 段)。委员会特别认为,中国应当“(a)审查目前的贷款偿还条件,确保借款国不会背负不可持续的债务……;(b)确保今后的贷款谈判符合国际最佳做法,以保护和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享受为目的,包括程序透明、没有腐败;(c)只向具有可持续成本效益比且需要使用借款国国内供应商和劳动力的项目发放贷款;(d)减少对有还款困难的借款国延长还款时间表和延长宽限期的依赖,更多地依赖重新谈判和/或取消债务;(e)确保附加条件对人权,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享受有积极贡献。” (第 23 段)作为《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委员会强调,中国同样负有域外义务,确保受“一带一路”项目影响的第三国尊重其享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 Board index
- All times are UTC
- Delete cookies
- Contact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