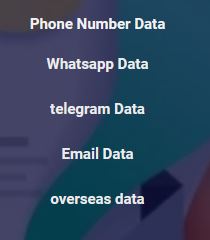与德国等“霸权”国家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 2011 年 9 月 7 日的裁决中所强调的那样,联邦议院必须“继续‘自主决定’,包括与预算收入(例如税收)和支出有关的决定,不受来自欧盟或其他成员国机构的外部约束”。
回到国内法,作者明确强调了对于我国宪法中第 1/2012 不同意见。他提出的问题既具有挑衅性又有充分的根据:“即使承认,在共同体和国际法的决定性推动下,我们必须制定严格的预算平衡监管纪律,首先只是‘热情’地建议(《欧洲+ 阿根廷电报号码数据 公约》 ),然后赋予其规定性(《财政契约条约》),那么,是否真的有必要通过宪法改革的主要途径将该纪律纳入意大利法律体系?”任何与共同体领域相关的法案都没有将财政可持续性以修改宪法作为条件。事实上,众所周知,财政 契约似乎预见了一种恩惠,而不是这种意义上的义务。事实上,我们谈论的是“具有约束力和永久性的规定,最好是宪法性的”,即使对于副词“最好”应该如何理解不乏不同意见。
作者并没有忽视宪法第14号的影响。关于自治制度的第 1/2012 号法令。受到质疑的是忠诚合作的原则,由于不同地区层级之间缺乏协调工具,忠诚合作原则遭到了侵蚀,而第 42/2009 号法律和随后的实施法令却体现了这一原则。
但还有更多。艺术。第 81 条第 6 款新案文中提到的“组织法”第 2 款第 5 条必须规定“在经济周期不利阶段或发生异常事件时,国家可采取哪些方法……即使在违反第 119 条的情况下,协助确保其他各级政府为履行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所固有的基本职能和基本履行义务提供资金”。这项规定实际上表明了“有关改革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宪法体系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如何使后者不再成为公共行动的最终和不可逾越的限制。这一预测“就好像意大利宪法明智地解决了政治与经济、公众希望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而二十世纪宪政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历经风雨,也一直在捍卫这些关系,但现在,这些关系却被彻底颠覆了”。
- Board index
- All times are UTC
- Delete cookies
- Contact us